木屋(18 木屋)
时间:2024/04/24 15:17:19 编辑: 浏览量:次
在北朝鲜的一处深山里,半山间有一座木屋。这座木屋被风雨剥蚀得成了灰褐色,就像使用了多年的木船,被搁置在山崖上。现在,彭总就正在这木屋里,背着手,踱来踱去。
这里是一座矿山。陈旧的木屋很像是矿山的办公处所。山下有一条小河,小河边有二三百户人家的一个村庄,大约是矿工们聚居的地方。由于战事紧迫,工人们已经撤退了,村子里显得十分空荡。从高山顶倾斜而下的高架矿斗缆线,上面挂着好几个运送矿石的吊斗,此刻一个一个地停在半空中。彭总踱着步子,有时在门口停住,望望山下空虚的村庄和空中凝滞不动的吊斗。尽管他一生饱经忧患,在战地看见过无数惨象,但今天看到这些,还是觉得心头沉重。
自从他奉令入京直到今天,才不过十多天的样子,脸上已经明显消瘦。这是由于过度的思考与紧张的活动所致。十月八日——也就是他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的当天,他就飞到了沈阳,第二天就召开了高级将领的会议;随后又乘火车赶到了安东,对各作战师的干部,做了动员和部署。十一日的晚上,他就飞回了北京,亲自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十二日一早,他连口气也没喘又飞回沈阳,接着又乘火车到了安东。这时候,他本来可以在江边稍事休息,可是考虑到朝鲜政府希望我迅速出动的要求,为了早一点同金日成首相取得联系,也早一点了解前方的情况,他就在部队出动的前一天——十月十八日黄昏出发了。前面由朝鲜外相乘坐的一辆华沙牌小轿车引导着,他同一个秘书和两个警卫员共乘一辆小吉普,后面跟着一辆中卡和一辆卡车,由参谋长带着一部电台和工作人员乘坐。就这样,在暮色苍茫中踏上了朝鲜的土地,沿着山间公路向前驰去。前天上午,赶到了一个僻静的山村,在路边一所农舍里会见了金日成首相。在这次历史性的战友的会见中,他们交谈了当前的战况和作战方针,以及成立联合司令部的问题,以后就转移到这里来了。
在这座小木屋里,他已经整整等了一天。此时,可以说他正经历着一种少有的焦急心情。因为敌人是机械化部队,进展相当迅速,而我各路大军却是徒步行军,前进得相当迟缓。据昨天了解的战况,我军秘密渡江的当天,美第八集团军已经攻占平壤。随后,麦克阿瑟乘坐飞机,亲自指挥伞兵部队于平壤以北距中朝边境八十英里的肃川、顺川降落,以截击朝鲜人民军的后路。按照预定计划,我军本来企图在龟城、泰川、球场洞、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构筑防线,阻住敌人,现在看很可能做不到了。另外志愿军的指挥机构和新任命的几个副司令员,正随同部队一起行动,还不知何时来到。还有一件不大也不小的事也使彭总心中不安,就是那辆携带电台的卡车,掉队了。开始还以为很快会赶上来,谁知过了一天多还渺无踪影。彭总的脸就沉下来了。
现在,这个指挥部的全部人马,就是一个秘书,两个警卫员和一个朝语翻译。为了保密,他们都已换上了朝鲜人民军的军服。警卫员小张正在木屋外的一棵大松树下烧水。新调来的警卫员小崔,是延边朝鲜族的一个青年战士,在旁边帮助他。从沈阳带来的一个很精致的煤油炉子,冒着蓝色的火苗,营营地歌唱着。秘书林青坐在松树下的一块大青石上,望望彭总的脸色,心里也不安起来,他长时间地凝望着山谷入口的地方,希望先头部队和载着电台的汽车能够奇迹般地出现。
白铁壶在深秋的寒风中冒着白汽,水开了。小张把祖国带来的饼干,还有特为彭总烤的馒头干拿出来,一面嘟哝着说:“早知道是这环境儿,从沈阳多带点东西来该有多好!”林青怕彭总听见这话,瞪了小张一眼,然后站起来,走到木屋的门口说:
“老总,已经九点多了,咱们开饭吧!”
彭总哼了一声,依然继续踱来踱去。
林青见彭总不动,又催了一句,彭总才慢腾腾地走出来,坐在那块大青石上。小张早把他那个使用了多年的旧茶缸刷洗干净,给他泡了一大缸子湖南绿茶。他随意吃了一块馒头干,就不吃了,只是一味地坐在那里喝茶。
这林青很能体察彭总的心理,一看他那两道浓眉几乎挤到一起去了,立刻宽解地说:
“我看电台可能很快就会上来。”
“本来昨天就该赶上来嘛,乱弹琴!”彭总不高兴地说,两个倔犟的嘴角也深深地弯了下来。
“很可能是走错路了;他们没带向导,又不懂话。”
彭总没说什么,似乎接受了这个解释。他喝了几口闷茶,又说:
“给两个团配了汽车,他们也该上来了嘛!”
这时有机群正从西面上空掠过,林青朝上一指说:
“就是有汽车也不行啊。白天不能走,晚上不敢开灯。也许还不如走路快哩!”
这时,金日成首相的指挥部派人送来两大草袋大米和一份特意用汉文书写的敌情通报。林青看着那份通报,不禁眉毛一扬几乎惊叫起来:
“哎呀,怎么到了我们后边去了?”
彭总一向不喜欢有人在指挥部表现出这种神态,他瞪了林青一眼,然后戴上老花眼镜,接过通报看起来。原来各路敌人都已经接近或越过了我们准备修筑防线的地区,尤其是西线东路的伪六师,已经越过熙川、桧木洞,正向楚山前进。他要过林青口袋里装着的那本袖珍地图一看,果然这路敌人已经到了现在指挥位置的右上方了。其他各路敌人也都逐渐逼近。
他再一次地陷到沉思里。过了半晌,他把地图交还林青,慢吞吞地站起身来,沿着一条山坡小道向上走去。林青一看彭总要上山,知道他心里着急,也不敢多问,就向小张使了个眼色,同小张一起,在后面紧紧跟上。
这时已是秋末冬初,浓艳的秋色已失去了昨日的光泽;加上暗云低垂,西风凄厉,更增添了一片萧森之气。山径上全是一层层的落叶,已由嫣红色变得紫郁郁的。树上的叶子还没有落净,一阵风来,飘飘飒飒,就像急雨一般落到地面。但是,在这暗淡的图画中,仍有一些灌木,密密地长着金灿灿的叶片,十分鲜亮,就像迎春花一般摇曳在秋风里。
彭总踏着厚厚的落叶在山径上走着。论爬山,在他年轻时那是没有比的;即是现在年已五十有二,这个征战半生的人,仍较常人为快。林青和小张在后面跟着,并不显得多么轻松。
彭总上到山顶,向南一望,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原来山下自南而北一条公路,断断续续都是逃难的人群。他们大部分是身着白衣的农民,有的牵着耕牛,有的赶着牛车。老老小小,走得十分迟慢。仔细看,也有不少城市打扮的人羼杂其间,很可能是从平壤等大城市撤退下来的。彭总看到这般情景,不由暗暗担心:目标这样大,如果敌机一来可怎么办!……正沉吟间,只听小张喊了一声:“敌机!”彭总举头一望,只见两架野马式战斗机,从山后像贼一般突袭过来。人群顷刻大乱,纷纷向公路两侧奔逃。可是公路上有一个人,好像吓傻了,他左盼右顾,只是站着不动。这时那两架野马式已经对准公路自南而北得意洋洋地扫射起来。公路上卜卜卜卜腾起一溜烟尘,烟尘过后,那个人已经倒伏在公路上了。彭总要过望远镜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壮年男子背着一个白发老翁,他们一起倒在黄土公路上,身旁流了一大摊血。
“这些狗娘养的!”彭总把望远镜递给小张,望着远去的敌机狠狠地骂了一句。小张望望彭总,见他的眼睛浮起一层微红,两个嘴角也搭拉下来。再看看望远镜接触眼圈的地方,湿漉漉的,似乎有泪水流过的样子,就掏出手帕来悄悄拭去,没有做声。
彭总转身向北望去,在公路的尽头,依然是连续不断的逃难的人流,连部队的影子也没有。面对着这样紧急的情况,他只好望着连绵的云山兴叹。
“我看老总还是回去吧!”善知人意的林青劝慰地说,“我一再计算,那个配备汽车的先头部队,至迟今晚也就到了。”
彭总依旧望着北方,没有做声。
“要不,这样——”林青笑着说,“首长先回去,我在这里望着;部队一来,我就去报告,也不误事。”
说到这里,彭总才勉强点了点头,缓步向山下走去。
果然,林青的计算不差,黄昏时分,第五军的先头团——邓军的团队已经开到。林青带着邓军来见彭总。邓军听说是去见一位首长,却不料踏进木屋一看,原来是彭总坐在那里。他不由自主地要举起右臂敬礼,肩膀只动了一动,才意识到自己早已失去了右臂。他似乎带着几分抱歉的神情行了一个立正注目礼,凝望着彭总。
“这是第五军的先头团团长邓军同志,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到。”林青高兴地介绍说。
“好,请坐,请坐!”
邓军的到来,显然使彭总喜出望外。他站起身来,满脸都是笑容,正要上前与邓军握手,才看出只是一个空空的袖管,就握住他的左手,亲热地说:
“怎么,你这个独臂将军也上阵了?”
邓军像小孩似的羞涩地一笑。
彭总等邓军坐定,见他多少还有些拘谨,就笑着说:
“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吧?”
“不,”邓军说,“长征路上,行军的时候我见过您;打兰州以前,我还听过您的动员报告。”
“你也参加打兰州了?”
“我这只膀子就是在那里丢的。”
“噢!”彭总回忆着说,“那个仗你们打得不错。我听说有一个团长很能打,就是爱跑到前面去打机枪,后来还负了重伤……是不是就是你哟?”
邓军红着脸笑了。由于他的面色过黑,那阵红潮也不大看得出来。
“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彭总宽慰地说,“如果你们再不来,可就误了大事。”
他说到这里,又问:
“不是给你们派了几十辆汽车吗?”
“差不多都让飞机给炸毁了,”邓军有些抱愧地说。“以后我们就徒步行军,战士们背得太重,加上粮食和干粮,总有五六十斤。”
彭总“唔”了一声,半晌没有言语,停了一会儿才说:
“确实苦了那些战士们……一个没有制空权,就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归根结底还是国家太穷哟!”
说到这里,他瞅了邓军一眼,又问:
“部队的情绪怎么样?”
“情绪蛮好。”邓军欣然回答,“不过,认识也不一样:一些人在国内打胜仗打惯了,把美军根本不放在眼里;一些人又因为同美军第一次作战,觉得心里没有底。个别怯战的人也有。”
“要特别加强政治工作,来发挥我们的优势!”彭总语气很重地说,“现在情况十分紧急。有一路敌人已经到我们后边去了。你们的任务没有变,要尽快插到龟城。如果龟城已经被敌人占领,你们就在龟城以北构筑阵地,来掩护后面的部队展开。”
“好!”邓军站起身来,表示庄严地受领了任务。
彭总把邓军送出门外,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
“要告诉同志们:我们友邦的存亡,我们祖国的安危,还有我们军队的荣辱,都在此一战!”
邓军立刻觉得心里热烘烘的,像有一股强有力的热流,在胸中激荡奔腾。当他走到山坡下的时候,还看见彭总站在那棵大松树下向他招手。
前面有了部队,彭总的心就放下了一半。但是电台没有上来,仍不免使他恼火。熬到第二天晚九时,参谋长和电台队长终于携电台一起到达。参谋长立刻来见彭总。
这个参谋长名叫夏文,是从兵团副司令中选调来的。他担任过团、师、军以至兵团的各级参谋长,富有参谋工作经验,知识面也颇为广博。他身量不高,面孔白皙,温文尔雅,颇有一点文人风度。彭总过去并不认识他,但在这次组织部队渡江工作中,见他思想很有条理,办事精细,已经留下了良好印象。夏文由于电台掉队,心中甚为不安;平时听说彭总非常严厉,更增加了几分胆怯。所以一见彭总,首先把遭到空袭汽车被打坏的情况详细作了报告,彭总只看了他两眼,并没有再说什么。他那悬着的心就放下了一半。接着他把路上收到的电报交给彭总,把当前的敌情和各路大军渡江后到达的位置,也做了详细汇报,彭总的脸色渐渐明朗起来,那威严的下垂的嘴角才开始有了松动。
“我们的行动,敌人到底发觉了没有?”他抬起脸,异常关切地问。
“没有。”夏文的语气十分肯定。
“那些外国通讯社的消息你全看了?”
“全看了。美国人不单没有讲到我们出兵,而且多次讲到我们不会出兵。”
彭总的脸色越发明亮起来,全神贯注地望着夏文。夏文兴致勃勃地讲道:
“有一则美联社的电讯很有意思。它说,在汉城被占之前,对我们是否出兵,确实有过一些揣测;但是,现在倒认为不可能了……”
“为什么?”
“他们说:如果中共打算干涉朝战的话,就会在汉城在共产党手中的时候或者至少平壤在他们手中的时候参加。在两个京城都被攻占之后,大家就断定中国无意干涉了……”
“蠢家伙!我们不是公开告诉他们,不能置之不理吗?”
“是的,是的,”夏文连声说,“可是他们有他们的逻辑。那则电讯还说:中国官员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在内,虽然作过一些刀剑铮铮的声明,从字义上毫无疑问地意味着,他们决不容许共产党朝鲜从地图上消失,可是许多有经验的观察家认为,有两个理由不能把这些声明照字面的意义接受。第一,因为正式出兵干涉,就会使共产党人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的一切希望归于消失;第二,因为毛泽东被认为非常狡黠,决不至于伸手到朝鲜的烈火中取出俄国的热栗子……”
夏文说着,从电报堆里取出那则电讯递给彭总,彭总看着看着,不自觉地微笑起来,说道:
“这些资产阶级!连他们的细胞也是利己主义。”
夏文也笑起来,继续说:
“从军事上,他们也不相信我们出兵。美国第十兵团的发言人说,‘要不首先把我们的空军遮住,中国就不会派大规模的陆上部队。’我们的二十几万大军,神不知鬼不觉地过了江,直到今天敌人一点也没有发觉,这在军事上也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彭总见他颇有得意之色,瞅了他一眼,严肃地说:
“这个大意不得!最好到大规模打响之前,一直不要敌人发觉。”
夏文汇报完了,彭总来回踱着步子。他沉思了好大一阵,才停住脚步缓缓地说:
“现在的敌情还很严重,主要是各路敌人差不多都越过了我们预定的防线,我们的部队除龟城以外,恐怕都赶不到了。毛主席原来让我们构成一道防线,守一个时期,准备明年春天反攻,现在看,这个计划恐怕要改变了。”
“计划要改变?”夏文惊讶地望着彭总。
“是的,要改变。”彭总点点头说,“因为情况变了。这几天我已经再三地考虑到这个问题。现在敌人对我估计不足,正在分兵冒进,正是我们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我看还是用我们的拿手好戏——打运动战,打歼灭战,选择敌人薄弱的一路,予以歼灭。”他说着,右手握拳向左掌心里狠狠一击,说得十分斩钉截铁,显然他的想法已经成熟。
“要拟定新的作战计划吗?”
“不,不忙。”彭总坐下来说,“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各位副司令员和副政委也许明天就会到吧,等他们来到,我们共同研究决定,然后再上报主席和军委批准。”
“好,好,”夏文说,“他们正随第三军行动,大约明天就可以来到。”
在夏文临离开这座木屋时,不自禁地以崇敬的目光,望了望这个身经数百战的人物,这个将要同他一同度过惊涛骇浪的人。心里悄悄地说:“他,确是实战经验丰富,善于临机应变,头脑机敏果断,确实名不虚传。”
几位副司令员和一位副政委,果于次日随同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的人员一起来到。他们就住在山坡下的那些农舍里。这个指挥机关是以一个兵团部为基础编成的,几个领导干部是从各个兵团选调的。第一副司令员秦鹏,十年内战时期就已崭露头角,到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是逐鹿中原、纵横大西南的名将了。他生得体魄魁伟,一副络腮胡子,颇有风采。特别是他那豪放不羁的性格,趣事轶闻之多,几乎风传全军。第二副司令员滕云汉,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立下不少战功。他是南方人的那种矮个子,但看去极为精干,军事上足智多谋,很有心计。文化程度虽不太高,但战斗经验极为丰富,他从战士、副班长、班长、副排长、排长,一直当到了兵团副司令,作战勇敢,指挥沉着果断,把他放到一条战线上,那条战线立刻就稳定了。第三副司令员冯慧,军事、政治、后勤工作全干过,尤其擅长后勤工作。他高高的个子,脸上还有几颗麻子,性格特别温和,很能与人相处,别人开多大玩笑,他也从不气恼。此外,就是那位副政委齐至真了。这个人坦率乐观,隔几间屋子就能听见他那响亮的笑声。他上过大学,留过洋,作了几十年的政治工作,还出过两本小册子,在政治工作上自然是一个专家了。在干部使用上,彭总一向主张五湖四海,不抱门户之见。他看到,从各个野战军选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干部,心里非常高兴。在第一次见面会上,他曾说,“敌人自称是‘联合国军’,其实,我们也是一个联合国哟!”而调来的这些干部,由于彭总在全军的崇高威望,从内心有一种崇敬之情。所以很自然地就形成了领导核心。在各位领导干部来了之后,当天就开了作战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一致通过了彭总的意见:准备利用敌人分兵冒进之机,机动歼敌。
会后,彭总就回到他的那个木屋中去了,其他人也都回到山下的农舍里。夏文还没有坐定,就听见远处有沉重的隆隆声,接着山头上又响起了尖厉的防空号音。他走到院中一看,一群一群的敌机正凌空而过,总有好几十架,气氛很不寻常。为了怕发生意外,他立即让参谋通知全直属队注意防空,还特意通知了各位首长。当他来到山坡下的防空洞时,看见各位首长都来了,唯独不见彭总。大家也正在心神不安地议论这事。有的说:“彭老总在国内打仗就不注意防空,现在这么多飞机,再不注意怎么行啊!”有的说:“仗还没有打起来,如果统帅部先出了事,那问题可就大了。”大家议论纷纷,一致要参谋长亲自去把彭总拉来。夏文听大家讲得有理,就急火火地走出洞口。
他上了山坡,走到木屋跟前,看见警卫员小张正站在那几棵松树下警惕地望着天空。夏文急冲冲地问:
“小张,你怎么不叫首长去防空啊?”
“你去叫吧!”小张哭丧着脸说。
“林秘书呢?他怎么不去叫?”
“哼,谁也不行。”
夏文踏进木屋,看见彭总端端地坐在案前,面前摆着一个半旧的四四方方的大铜墨盒,正手执毛笔聚精会神地写着什么。林青无可奈何地坐在一边。尽管外面飞机的隆隆声震得窗纸索索颤抖,但对于这个光着头鬓角露出白发的老军人,却仿佛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事情。
“彭总……”夏文低声试探地叫。
“你有事吗?”彭总摆摆头示意让他坐下。
“没有事……今天的飞机特别多……”
“唔,很可能敌人的攻势要开始了。”
他说着,头也不抬,把笔伸进墨盒蘸得饱饱的,又继续写下去。
夏文不忍打断他的思路,等他把几句写完,才又慢吞吞地说:
“我看飞机太多,今天得注意了……”
“是的!决不要大意。”彭总边写边说,“要告诉大家注意防空!”
“老总,我说的是您呀!”
“我?”彭总偏过头笑笑,“你们先去。你知道,我正给毛主席写那封电报。”说过,又写下去。
夏文一时语塞。这时,一架敌机声音很大,仿佛已经飞到头顶。远处还响起了沉重的炸弹声。夏文灵机一动,一面上前去盖墨盒,一面乘势说:
“还是到防空洞写吧,你瞧要下蛋了。”
彭总这才离开座位,推开门,仰起脸向上一望,只见一架敌机哇的一声掠了过去。他翻翻眼骂道:
“好个狗娘养的,看你能把老子吃了!”
他手里仍旧拿着那管戴月轩精制的七紫三羊毫的毛笔,站在那里观望了一会,用笔指了指山那边盘旋的敌机,笑着对夏文说:
“我的参谋长!你瞧,目标根本不在这里嘛!”说过,又从容地回到座位,伏在桌案上。
敌机在山那边狂轰滥炸了一顿,纷纷离去。彭总的电报已经写就。这已经是他多年的习惯,凡重要的电报都是亲自动手。写完他又细细地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才交给夏文说:
“这是第一次战役的设想。请几位副司令和副政委都看一下,一个也不要漏掉。大家没有意见,再发出去。”
夏文拿着电报,走出了木屋。冷风一吹,他才发觉自己额头上都是汗水。他掏出手帕擦了擦,觉得背上也凉浸浸的,原来衬衣也早让汗水湿透了。当他走下山坡的时候,回过头望了望那座风雨剥蚀的木屋,觉得它更像是一只在惊涛骇浪中的船只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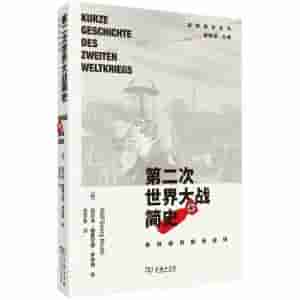
-
二战是哪一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简史)
浏览:29 2024-05-09
-

-
孙俪微博(孙俪发微博,晒8岁儿子与邓超的对话,网友大笑:能自力更生了)
浏览:32 2024-05-09
-

-
含有兔的字(“钱”“兔”无量、大展鸿“兔”……谐音梗祝福语火遍全网)
浏览:27 2024-05-09
-

-
月上中天(定风波:词林正韵五阕)
浏览:25 2024-05-09
-

-
香港一级黄色片(她为了红不惜拍大尺度片,性感豪放大胆敢脱敢露)
浏览:24 2024-05-09
-

-
上市时间(上市之路一波三折,留给万达商管的时间不多了?)
浏览:25 2024-05-09